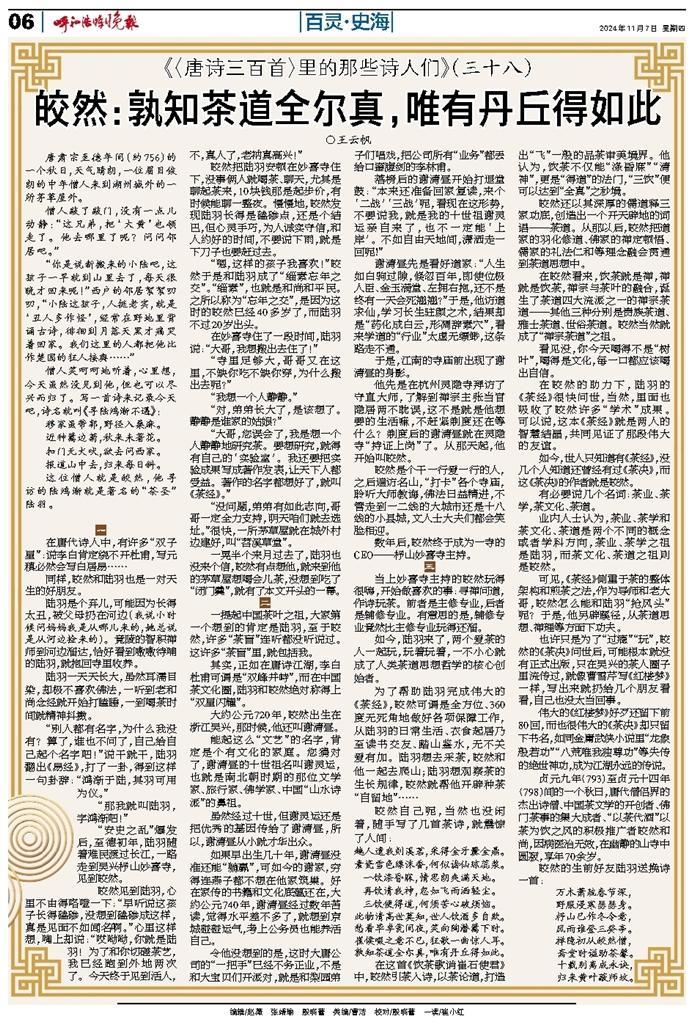○王云帆
唐肃宗至德年间(约756)的一个秋日,天气晴朗,一位眉目俊朗的中年僧人来到湖州城外的一所茅草屋外。
僧人敲了敲门,没有一点儿动静:“这兄弟,把‘大黄’也领走了。他去哪里了呢?问问邻居吧。”
“你是说新搬来的小陆吧,这孩子一早就到山里去了,每天很晚才回来呢!”西户的邻居絮絮叨叨,“小陆这孩子,人挺老实,就是‘丑人多作怪’,经常在野地里背诵古诗,徘徊到月落天黑才痛哭着回家。我们这里的人都把他比作楚国的狂人接舆……”
僧人笑呵呵地听着,心里想,今天虽然没见到他,但也可以尽兴而归了。写一首诗来记录今天吧,诗名就叫《寻陆鸿渐不遇》:
移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
近种篱边菊,秋来未著花。
扣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
报道山中去,归来每日斜。
这位僧人就是皎然,他寻访的陆鸿渐就是著名的“茶圣”陆羽。
一
在唐代诗人中,有许多“双子星”:说李白肯定绕不开杜甫,写元稹必然会写白居易……
同样,皎然和陆羽也是一对天生的好朋友。
陆羽是个弃儿,可能因为长得太丑,被父母扔在河边(我说小时候问妈妈我是从哪儿来的,她总说是从河边捡来的)。竟陵的智积禅师到河边溜达,恰好看到嗷嗷待哺的陆羽,就抱回寺里收养。
陆羽一天天长大,虽然耳濡目染,却极不喜欢佛法,一听到老和尚念经就开始打瞌睡,一到喝茶时间就精神抖擞。
“别人都有名字,为什么我没有?算了,谁也不问了,自己给自己起个名字吧!”说干就干,陆羽翻出《易经》,打了一卦,得到这样一句卦辞:“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
“那我就叫陆羽,字鸿渐吧!”
“安史之乱”爆发后,至德初年,陆羽随着难民渡过长江,一路走到吴兴杼山妙喜寺,见到皎然。
皎然见到陆羽,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早听说这孩子长得磕碜,没想到磕碜成这样,真是见面不如闻名啊。”心里这样想,嘴上却说:“哎呦呦,你就是陆羽!为了和你切磋茶艺,我已经跑到外地两次了。今天终于见到活人,不,真人了,老衲真高兴!”
皎然把陆羽安顿在妙喜寺住下,没事俩人就喝茶、聊天,尤其是聊起茶来,10块钱那是起步价,有时候能聊一整夜。慢慢地,皎然发现陆羽长得是磕碜点,还是个结巴,但心灵手巧,为人诚实守信,和人约好的时间,不要说下雨,就是下刀子也要赶过去。
“嗯,这样的孩子我喜欢!”皎然于是和陆羽成了“缁素忘年之交”。“缁素”,也就是和尚和平民。之所以称为“忘年之交”,是因为这时的皎然已经40多岁了,而陆羽不过20岁出头。
在妙喜寺住了一段时间,陆羽说:“大哥,我想搬出去住了!”
“寺里足够大,哥哥又在这里,不缺你吃不缺你穿,为什么搬出去呢?”
“我想一个人静静。”
“对,弟弟长大了,是该想了。静静是谁家的姑娘?”
“大哥,您误会了,我是想一个人静静地研究茶。要想研究,就得有自己的‘实验室’。我还要把实验成果写成著作发表,让天下人都受益。著作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茶经》。”
“没问题,弟弟有如此志向,哥哥一定全力支持,明天咱们就去选址。”很快,一所茅草屋就在城外村边建好,叫“苕溪草堂”。
一晃半个来月过去了,陆羽也没来个信,皎然有点想他,就来到他的茅草屋想喝会儿茶,没想到吃了“闭门羹”,就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二
一提起中国茶叶之祖,大家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陆羽,至于皎然,许多“茶盲”连听都没听说过。这许多“茶盲”里,就包括我。
其实,正如在唐诗江湖,李白杜甫可谓是“双峰并峙”,而在中国茶文化圈,陆羽和皎然绝对称得上“双星闪耀”。
大约公元720年,皎然出生在浙江吴兴,那时候,他还叫谢清昼。
能起这么“文艺”的名字,肯定是个有文化的家庭。您猜对了,谢清昼的十世祖名叫谢灵运,也就是南北朝时期的那位文学家、旅行家、佛学家、中国“山水诗派”的鼻祖。
虽然经过十世,但谢灵运还是把优秀的基因传给了谢清昼,所以,谢清昼从小就才华出众。
如果早出生几十年,谢清昼没准还能“躺赢”,可如今的谢家,穷得连燕子都不想在他家筑巢。好在家传的书籍和文化底蕴还在,大约公元740年,谢清昼经过数年苦读,觉得水平差不多了,就想到京城碰碰运气,考上公务员也能养活自己。
令他没想到的是,这时大唐公司的“一把手”已经不务正业,不是和大宝贝们开派对,就是和梨园弟子们唱戏,把公司所有“业务”都丢给口蜜腹剑的李林甫。
落榜后的谢清昼开始打退堂鼓:“本来还准备回家复读,来个‘二战’‘三战’呢,看现在这形势,不要说我,就是我的十世祖谢灵运亲自来了,也不一定能‘上岸’。不如自由天地间,潇洒走一回呢!”
谢清昼先是看好道家:“人生如白驹过隙,倏忽百年,即使位极人臣、金玉满堂、左拥右抱,还不是终有一天会死翘翘?”于是,他访道求仙,学习长生驻颜之术,结果却是“药化成白云,形凋辞素穴”,看来学道的“行业”太虚无缥缈,这条路走不通。
于是,江南的寺庙前出现了谢清昼的身影。
他先是在杭州灵隐寺拜访了守直大师,了解到禅宗主张当官隐居两不耽误,这不是就是他想要的生活嘛,不赶紧剃度还在等什么?剃度后的谢清昼就在灵隐寺“持证上岗”了。从那天起,他开始叫皎然。
皎然是个干一行爱一行的人,之后遍访名山,“打卡”各个寺庙,聆听大师教诲,佛法日益精进,不管走到一二线的大城市还是十八线的小县城,文人士大夫们都会笑脸相迎。
数年后,皎然终于成为一寺的CEO——杼山妙喜寺主持。
三
当上妙喜寺主持的皎然玩得很嗨,开始做喜欢的事:寻禅问道,作诗玩茶。前者是主修专业,后者是辅修专业。有意思的是,辅修专业竟然比主修专业玩得还溜。
如今,陆羽来了,两个爱茶的人一起玩,玩着玩着,一不小心就成了人类茶道思想哲学的核心创始者。
为了帮助陆羽完成伟大的《茶经》,皎然可谓是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做好各项保障工作,从陆羽的日常生活、衣食起居乃至读书交友、踏山鉴水,无不关爱有加。陆羽想去采茶,皎然和他一起去爬山;陆羽想观察茶的生长规律,皎然就帮他开辟种茶“自留地”……
皎然自己呢,当然也没闲着,随手写了几首茶诗,就震惊了人间:
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牙爨金鼎。
素瓷雪色缥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
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
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
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
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在这首《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中,皎然引茶入诗,以茶论道,打造出“飞”一般的品茶审美境界。他认为,饮茶不仅能“涤昏寐”“清神”,更是“得道”的法门,“三饮”便可以达到“全真”之秒境。
皎然还以其深厚的儒道释三家功底,创造出一个开天辟地的词语——茶道。从那以后,皎然把道家的羽化修道、佛家的禅定顿悟、儒家的礼法仁和等理念融会贯通到茶道思想中。
在皎然看来,饮茶就是禅,禅就是饮茶,禅宗与茶叶的融合,诞生了茶道四大流派之一的禅宗茶道——其他三种分别是贵族茶道、雅士茶道、世俗茶道。皎然当然就成了“禅宗茶道”之祖。
看见没,你今天喝得不是“树叶”,喝得是文化,每一口都应该喝出自信。
在皎然的助力下,陆羽的《茶经》很快问世,当然,里面也吸收了皎然许多“学术”成果。可以说,这本《茶经》就是两人的智慧结晶,共同见证了那段伟大的友谊。
如今,世人只知道有《茶经》,没几个人知道还曾经有过《茶决》,而这《茶决》的作者就是皎然。
有必要说几个名词:茶业、茶学,茶文化、茶道。
业内人士认为,茶业、茶学和茶文化、茶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或者学科方向,茶业、茶学之祖是陆羽,而茶文化、茶道之祖则是皎然。
可见,《茶经》侧重于茶的整体架构和煎茶之法,作为导师和老大哥,皎然怎么能和陆羽“抢风头”呢?于是,他另辟蹊径,从茶道思想、禅理等方面下功夫。
也许只是为了“过瘾”“玩”,皎然的《茶决》问世后,可能根本就没有正式出版,只在吴兴的茶人圈子里流传过,就像曹雪芹写《红楼梦》一样,写出来就扔给几个朋友看看,自己也没太当回事。
伟大的《红楼梦》好歹还留下前80回,而也很伟大的《茶决》却只留下书名,如同金庸武侠小说里“龙象般若功”“八荒唯我独尊功”等失传的绝世神功,成为江湖永远的传说。
贞元九年(793)至贞元十四年(798)间的一个秋日,唐代僧侣界的杰出诗僧、中国茶文学的开创者、佛门茶事的集大成者、“以茶代酒”以茶为饮之风的积极推广者皎然和尚,因病医治无效,在幽静的山寺中圆寂,享年70余岁。
皎然的生前好友陆羽送挽诗一首:
万木萧疏春节深,
野服浸寒瑟瑟身。
杼山已作冬令意,
风雨谁登三癸亭。
禅隐初从皎然僧,
斋堂时谥助茶馨。
十载别离成永诀,
归来黄叶蔽师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