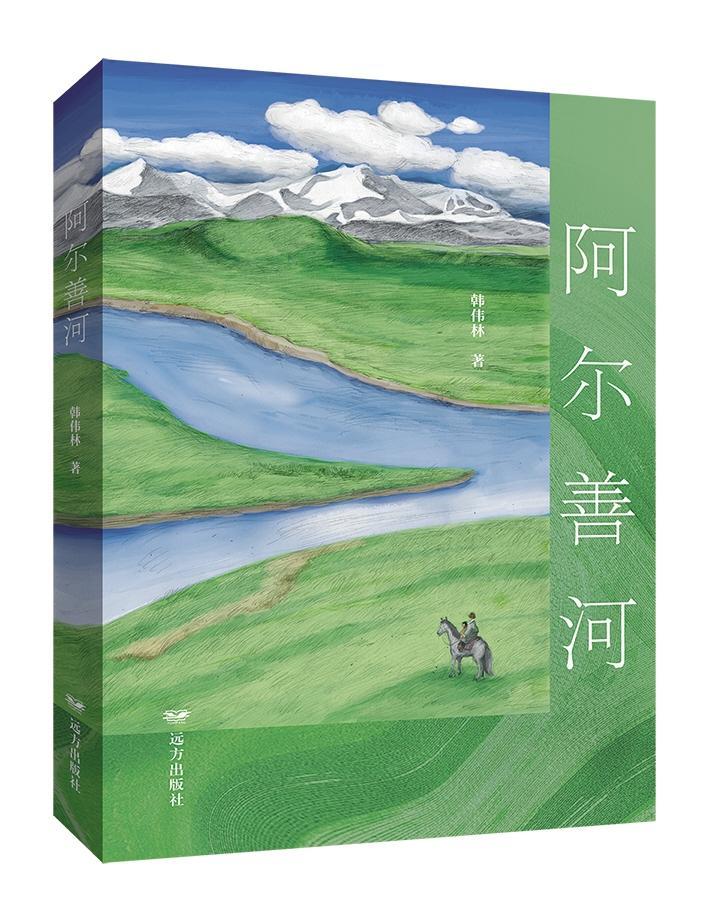■宋然
(二)自然与历史同构
在《阿尔善河》中,我们不难看到,作家韩伟林通过象征使自然糅合了复杂的意蕴,自然以与人类平等的身份下场影响历史的走向和故事的发展,自然被融入到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叙述中,因此,当历史的飓风掠过阿尔善草原的上空,草原上的草、木、人、畜无一不颤抖呼号,随着时代变迁或家族命运的演化,草原儿女诉不完的爱恨情仇、命运遭际,都与这里的自然规律共振。
作家在《阿尔善河》中大量运用闪回和插叙,在非线性的叙事方式中忽然闪现的自然承担了连接和推动叙事的重要任务。在多条时间线的交织中,并置出现的不同自然事物串联起来,勾勒出作品中描述的时间与空间,进而构建起一个立体的故事世界。如,小说并不是一开始就直接讲述阿尔善草原的历史,而是通过阿勇嘎带来好消息,永青扎布借口出去放牧,顺势将视线转移至草原,沿着阿尔善河一路向前,记忆不断闪回,由此开启对永青扎布送马、遭匪、与自治学院文艺宣传队结缘进而参与革命这段往事和历史的回忆。再如,植物学研究者阿古拉在罕乌拉山北坡发现一种优良牧草,当他带回去给永青扎布看过后,永青扎布大吃一惊,“脸红脖子粗,慌张站起来,有些喘不过气来,踱步出去透气,转身又折返回来,好像不可告人的秘密被人当场揭穿。幸好陶脑上的毡子只揭开一小半,包里的暗,收藏了他于暗处的慌张。”因为“这是金香告诉他的一剂香方的关键配方!”于是通过一株牧草,因病去世的金香仿佛死而复生般重新回归到读者视线,那段少女用生命制香的岁月随之扑面而来。金香身死多年以后,一株牧草尚且能如此牵动永青扎布的心,他对金香深沉真挚的感情跃然纸上。不仅如此,罕乌拉山北坡还无可救药地燃烧着阿古拉的心,那里不仅是他采集到宝贵植物种属标本的地方,更藏着一段深刻的人生记忆。于是对历史的回忆,便又通过自然的闪现缓缓展开,过去的历史与当下甚至未来的历史通过自然的参与被和谐地缝合在一起,“历时性”事件在似乎没有联系的情况下因自然的参与而产生出某种羁绊,正如在尾声中写道,“阿尔善草原进入了沉沉的梦乡”,梦从两千多年前就开始了,两千多年前的张骞以胡杨枝为节杖,被紫花苜蓿所吸引,带着亲自采集的种子踏上回乡的道路。但“历史的号角依是远去了。紫花苜蓿一路放飞,管它什么上古中古,还是今世,只管延绵流芳。”在现代,“它和全国各地特有的野生种质资源,共同培育出了更多的优良品种,生于田边、路旁、旷野以及河岸沟谷。”历史话语中不断闪现的自然描摹使作家获得了一种更具亲和力的方式,借助这种方式,作家在描述过去历史的同时也在以自己的想法描述当下的时代。在自然和历史的同构中,《阿尔善河》植根于即时之境,挣脱时空的桎梏,于历史长河中萃取其本质的精髓。
二 激活生态书写的诗意魅力
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加速推进,内蒙古地区的文学创作者积极响应。他们的创作蕴含着浓厚的危机感与生态忧虑,旨在唤醒公众对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促使人们反思自我内心世界。作家韩伟林在《民族文学》2019年第3期上曾发表过一篇名为《阿尔善河水长又清》的小说,小说以苏和与图雅这两位年轻人的爱情故事为序幕,巧妙地将笔触深入至阿尔善河这一自然纽带,深刻描绘了它与牧民朝克家族数代人之间不可分割的命运交织。2023年12月,长篇小说《阿尔善河》出版,小说共十一章,《阿尔善河水长又清》作为第八章被囊括其中。除了篇幅增加,主人公被重新安排,有了更加完整和具体的生活轨迹和命运发展叙述之外,细腻生动的历史书写令人格外侧目。两部作品在立足草原生态保护与资源开发利用这一主题上不谋而合,但不同于将目光投射于追踪关注当代社会草原生态后续发展问题,作家韩伟林为这一故事增添了更为广阔厚重的历史背景,这意味着在这部作品中历史书写与生态书写也存在着良性互动:
(一)写作逻辑“文学化”
“感时而发”这一中国文学的强势基因被内蒙古作家继承,他们笔下的生态书写实际上出于作家们对于国家民族生存所面临的“另一种危机”的忧患情怀。
在《阿尔善河》中,大量历史话语的参与首先就在人物塑造上提出了与生态书写不同的要求,即主人公应该拥有更具体更厚重的人物背景,使读者通常能够在阅读历史的过程中发现隐藏在人物背后复杂而又清晰的成长轨迹,人物的精神内涵在历史变迁、命运浮沉中能够立体展现。努尔金作为草原儿女的后代,在父辈谆谆教诲中自觉地承担起草原的生死荣辱。生态治理中,更是经历了多次思想转变,从一开始信心满满地认为通过发展工业能使家乡增收致富,到经历入狱、亲人朋友误解、阿尔善河断流等后的大彻大悟,最终摸索出一条朴素的生态学原理:生态与生产的关系“一定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适应与和谐才是目标。”草原、阿尔善河、罕乌拉山等自然景物生存状态的变迁,在历史的层面一定程度也推动着人物的自我反思,使努尔金不断接受现实与信念的拷问。吴楚克曾经憎恨父亲把她放置在无趣的草原深处,但在阿尔善草原腹地,她“看到了山之茂密,看到了草木的宝藏,看到了牧人波澜不惊的生活。”于是最终成为金香口中的那个人,肩负起了传承制香的责任。由此可见,使人物性格发生转变的不仅是单单某个事件的影响,其背后是草原深沉历史的沁润。
小说情节上,《阿尔善河》也别出心裁地设计了班先生与夫人捡到漂流瓶的故事,并在故事结尾刻意安排班夫妇与永青扎布的会面。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北方阿尔善草原家族几代人命运更替的同时,远在东南亚某国的陌生人夫妇正不遗余力地探寻着这一家族背后的故事与踪迹,并由此揭开一段隐秘的历史。这一情节的叙述相较于小说关于展现草原历史、书写几代人命运纠葛的部分似乎极为省略,然而,去繁从简,引人深思,耐人寻味。班先生“决定留下来走一走,看一看,准备回去把中国北方阿尔善草原上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读者可以想见,在生态保护背景下,这一家族的故事是否会被传播得更远更远。
(二)理性思考“深入化”
《阿尔善河》相较于其他作品,在理性思考自然生命背后的内在精神,深度挖掘精神生态与文化生态方面显然棋高一着。这要求作家选择更自由、更独到的视角与言说方式切入,恰到好处的历史书写很好地完成了这一课题。
在小说接近结尾之处,嘎查组织青壮牧民前往劳模杭盖家取经,根深蒂固的传统养殖观念在实实在在的收益面前被缓缓撼动。巴特尔和小革命讨论着杭盖家生产与生态模式的可借鉴性,小说恰得其时地插入一大段感慨与思考,将生产经营模式的问题上升到草原历史更替以及人生命运变迁的体悟,相比于过分强调对现实自然生态的干预和呼告,以及对错误生产与生态经营模式的发泄式说教,从历史和人生的角度考察牧民的观念转变为作品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表达空间,情感上也能迅速引起读者的共鸣。在说到阿尔善草原游牧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时,阿勇嘎在孙子孙媳妇鼓动下再次回到这片他魂牵梦萦的草原。在面对持续而来的生态危机时,关于生态悲剧的思考在努尔金的心里拥有了历史、生命以及深层生态哲学的意义,文中这样写道,“在努尔金随之而来的思索里,历史与现实交织,神话和哲学思想融合,草原特有的静与动、方与圆、多与少、人与自然、意志与智慧、传统与现代,一一对接。那些过去的历史在浩瀚的无穷世界如同瞬间,新一茬青草郁郁葱葱,草原又开始了新一轮环圆形周期活动,于现实的天幕,以一种思想的方式不断隐现。无论怎样,提供人们一个立场。他相信,一万年后,人类还会需要草原。”对草原生态问题见微知著地体察以及曲径通幽地探析,比直白地宣告生态观念、明确地表达焦虑更能展现文本的魅力,生态书写也能在现实生态危机的多重矛盾张力中以更灵巧的姿态实现困境的突围。(作者系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