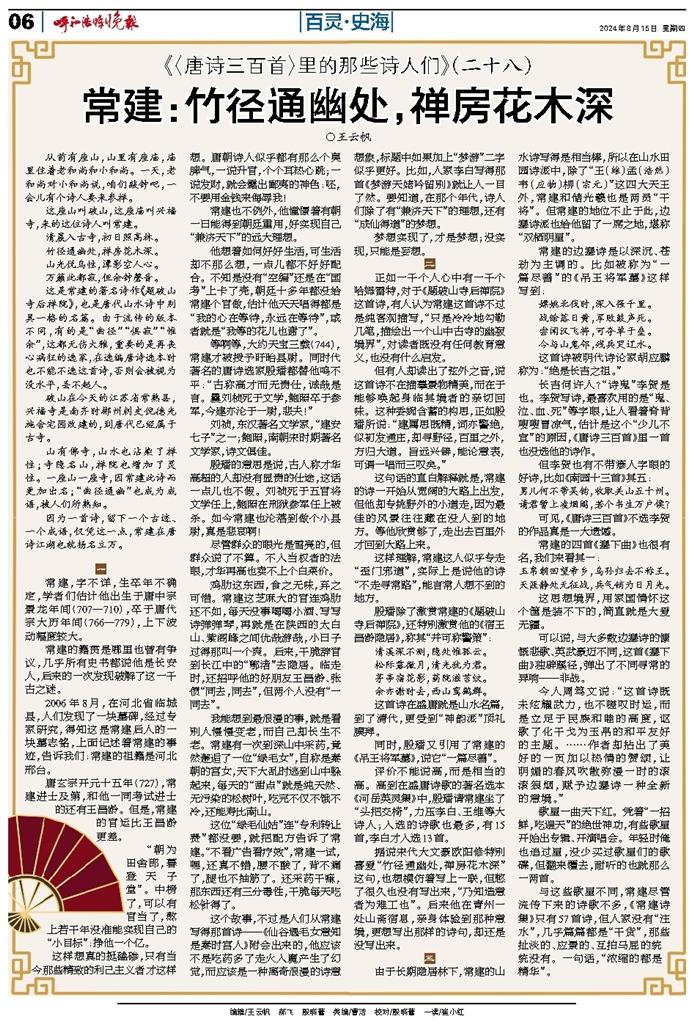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住着老和尚和小和尚。一天,老和尚对小和尚说,咱们敲钟吧,一会儿有个诗人要来参禅。
这座山叫破山,这座庙叫兴福寺,来的这位诗人叫常建。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
这是常建的著名诗作《题破山寺后禅院》,也是唐代山水诗中别具一格的名篇。由于流传的版本不同,有的是“曲径”“俱寂”“惟余”,这都无伤大雅,重要的是再丧心病狂的选家,在选编唐诗选本时也不能不选这首诗,否则会被视为没水平,丢不起人。
破山在今天的江苏省常熟县,兴福寺是南齐时郴州刺史倪德光施舍宅园改建的,到唐代已经属于古寺。
山有佛寺,山水也沾染了禅性;寺隐名山,禅院也增加了灵性。一座山一座寺,因常建此诗而更加出名;“曲径通幽”也成为成语,被人们所熟知。
因为一首诗,留下一个古迹、一个成语,仅凭这一点,常建在唐诗江湖也就扬名立万。
一
常建,字不详,生卒年不确定,学者们估计他出生于唐中宗景龙年间(707—710),卒于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上下波动幅度较大。
常建的籍贯是哪里也曾有争议,几乎所有史书都说他是长安人,后来的一次发现破解了这一千古之谜。
2006年8月,在河北省临城县,人们发现了一块墓碑,经过专家研究,得知这是常建后人的一块墓志铭,上面记述着常建的事迹,告诉我们:常建的祖籍是河北邢台。
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常建进士及第,和他一同考试进士的还有王昌龄。但是,常建的官运比王昌龄更差。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中榜了,可以有官当了,熬上若干年没准能实现自己的“小目标”:挣他一个亿。
这样想真的挺磕碜,只有当今那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才这样想。唐朝诗人似乎都有那么个臭脾气,一说升官,个个耳热心跳;一说发财,就会露出鄙夷的神色:呸,不要用金钱来侮辱我!
常建也不例外,他憧憬着有朝一日能得到朝廷重用,好实现自己“兼济天下”的远大理想。
他想着如何好好生活,可生活却不那么想,一点儿都不好好配合。不知是没有“空编”还是在“国考”上卡了壳,朝廷十多年都没给常建个官做,估计他天天唱得都是“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或者就是“我等的花儿也谢了”。
等啊等,大约天宝三载(744),常建才被授予盱眙县尉。同时代著名的唐诗选家殷璠都替他鸣不平:“古称高才而无贵仕,诚哉是言。曩刘桢死于文学,鲍照卒于参军,今建亦沦于一尉,悲夫!”
刘祯,东汉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鲍照,南朝宋时期著名文学家,诗文俱佳。
殷璠的意思是说,古人称才华高超的人却没有显贵的仕途,这话一点儿也不假。刘祯死于五官将文学任上,鲍照在刑狱参军任上被杀。如今常建也沦落到做个小县尉,真是悲哀啊!
尽管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但群众说了不算。不入当权者的法眼,才华再高也卖不上个白菜价。
鸡肋这东西,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常建这芝麻大的官连鸡肋还不如,每天没事喝喝小酒、写写诗弹弹琴,再就是在陕西的太白山、紫阁峰之间优哉游哉,小日子过得那叫一个爽。后来,干脆辞官到长江中的“鄂渚”去隐居。临走时,还招呼他的好朋友王昌龄、张偾“同去,同去”,但两个人没有“一同去”。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看别人慢慢变老,而自己却长生不老。常建有一次到深山中采药,竟然邂逅了一位“绿毛女”,自称是秦朝的宫女,天下大乱时逃到山中躲起来,每天的“甜点”就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松树叶,吃完不仅不饿不冷,还能寿比南山。
这位“绿毛仙姑”连“专利转让费”都没要,就把配方告诉了常建。“不看广告看疗效”,常建一试,嘿,还真不错,腰不酸了,背不痛了,腿也不抽筋了。还采药干嘛,那东西还有三分毒性,干脆每天吃松针得了。
这个故事,不过是人们从常建写得那首诗——《仙谷遇毛女意知是秦时宫人》附会出来的,他应该不是吃药多了走火入魔产生了幻觉,而应该是一种离奇浪漫的诗意想象,标题中如果加上“梦游”二字似乎更好。比如,人家李白写得那首《梦游天姥吟留别》就让人一目了然。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诗人们除了有“兼济天下”的理想,还有“成仙得道”的梦想。
梦想实现了,才是梦想;没实现,只能是妄想。
二
正如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题破山寺后禅院》这首诗,有人认为常建这首诗不过是纯客观描写,“只是冷冷地勾勒几笔,描绘出一个山中古寺的幽寂境界”,对读者既没有任何教育意义,也没有什么启发。
但有人却读出了弦外之音,说这首诗不在描摹景物精美,而在于能够唤起身临其境者的亲切回味。这种委婉含蓄的构思,正如殷璠所说:“建属思既精,词亦警绝,似初发通庄,却寻野径,百里之外,方归大道。旨远兴僻,能论意表,可谓一唱而三叹矣。”
这句话的直白解释就是,常建的诗一开始从宽阔的大路上出发,但他却专挑野外的小道走,因为最佳的风景往往藏在没人到的地方。等他欣赏够了,走出去百里外才回到大路上来。
这样理解,常建这人似乎专走“歪门邪道”,实际上是说他的诗“不走寻常路”,能言常人想不到的地方。
殷璠除了激赏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还特别激赏他的《宿王昌龄隐居》,称其“并可称警策”:
清溪深不测,隐处惟孤云。
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
茅亭宿花影,药院滋苔纹。
余亦谢时去,西山鸾鹤群。
这首诗在盛唐就是山水名篇,到了清代,更受到“神韵派”顶礼膜拜。
同时,殷璠又引用了常建的《吊王将军墓》,说它“一篇尽善”。
评价不能说高,而是相当的高。高到在盛唐诗歌的著名选本《河岳英灵集》中,殷璠请常建坐了“头把交椅”,力压李白、王维等大诗人;入选的诗歌也最多,有15首,李白才入选13首。
据说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特别喜爱“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这句,也想模仿着写上一联,但憋了很久也没有写出来,“乃知造意者为难工也”。后来他在青州一处山斋宿息,亲身体验到那种意境,更想写出那样的诗句,却还是没写出来。
三
由于长期隐居林下,常建的山水诗写得是相当棒,所以在山水田园诗派中,除了“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这四大天王外,常建和储光羲也是两员“干将”。但常建的地位不止于此,边塞诗派也给他留了一席之地,堪称“双栖明星”。
常建的边塞诗是以深沉、苍劲为主调的。比如被称为“一篇尽善”的《吊王将军墓》这样写到:
嫖姚北伐时,深入强千里。
战馀落日黄,军败鼓声死。
尝闻汉飞将,可夺单于垒。
今与山鬼邻,残兵哭辽水。
这首诗被明代诗论家胡应麟称为:“绝是长吉之祖。”
长吉何许人?“诗鬼”李贺是也。李贺写诗,最喜欢用的是“鬼、泣、血、死”等字眼,让人看着脊背嗖嗖冒凉气,估计是这个“少儿不宜”的原因,《唐诗三百首》里一首也没选他的诗作。
但李贺也有不带瘆人字眼的好诗,比如《南园十三首》其五: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可见,《唐诗三百首》不选李贺的作品真是一大遗憾。
常建的四首《塞下曲》也很有名,我们来看其一:
玉帛朝回望帝乡,乌孙归去不称王。
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
这思想境界,用家国情怀这个筐是装不下的,简直就是大爱无疆。
可以说,与大多数边塞诗的慷慨悲歌、英武豪迈不同,这首《塞下曲》独辟蹊径,弹出了不同寻常的异响——非战。
今人周笃文说:“这首诗既未炫耀武力,也不嗟叹时运,而是立足于民族和睦的高度,讴歌了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友好的主题。……作者却拈出了美好的一页加以热情的赞颂,让明媚的春风吹散弥漫一时的滚滚狼烟,赋予边塞诗一种全新的意境。”
歌星一曲天下红。凭着“一招鲜,吃遍天”的绝世神功,有些歌星开始出专辑、开演唱会。年轻时俺也追过星,没少买过歌星们的歌碟,但翻来覆去,耐听的也就那么一两首。
与这些歌星不同,常建尽管流传下来的诗歌不多,《常建诗集》只有57首诗,但人家没有“注水”,几乎篇篇都是“干货”,那些扯淡的、应景的、互拍马屁的统统没有。一句话,“浓缩的都是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