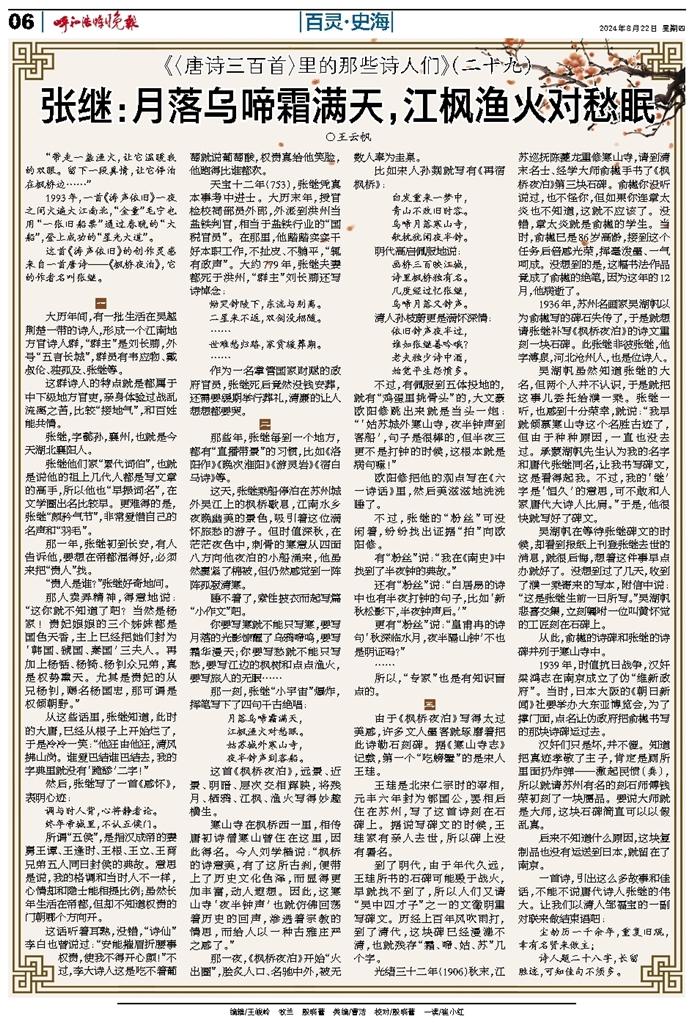○王云帆
“带走一盏渔火,让它温暖我的双眼。留下一段真情,让它停泊在枫桥边……”
1993年,一首《涛声依旧》一夜之间火遍大江南北,“金童”毛宁也用“一张旧船票”通过春晚的“大船”,登上成功的“星光大道”。
这首《涛声依旧》的创作灵感来自一首唐诗——《枫桥夜泊》,它的作者名叫张继。
一
大历年间,有一批生活在吴越荆楚一带的诗人,形成一个江南地方官诗人群,“群主”是刘长卿,外号“五言长城”,群员有韦应物、戴叔伦、独孤及、张继等。
这群诗人的特点就是都属于中下级地方官吏,亲身体验过战乱流离之苦,比较“接地气”,和百姓能共情。
张继,字懿孙,襄州,也就是今天湖北襄阳人。
张继他们家“累代词伯”,也就是说他的祖上几代人都是写文章的高手,所以他也“早振词名”,在文学圈出名比较早。更难得的是,张继“颇矜气节”,非常爱惜自己的名声和“羽毛”。
那一年,张继初到长安,有人告诉他,要想在帝都混得好,必须来把“贵人”找。
“贵人是谁?”张继好奇地问。
那人卖弄精神,得意地说:“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当然是杨家!贵妃娘娘的三个姊妹都是国色天香,主上已经把她们封为‘韩国、虢国、秦国’三夫人。再加上杨铦、杨锜、杨钊众兄弟,真是权势熏天。尤其是贵妃的从兄杨钊,赐名杨国忠,那可谓是权倾朝野。”
从这些话里,张继知道,此时的大唐,已经从根子上开始烂了,于是冷冷一笑:“他狂由他狂,清风拂山岗。谁爱巴结谁巴结去,我的字典里就没有‘跪舔’二字!”
然后,张继写了一首《感怀》,表明心迹:
调与时人背,心将静者论。
终年帝城里,不认五侯门。
所谓“五侯”,是指汉成帝的妻舅王谭、王逢时、王根、王立、王商兄弟五人同日封侯的典故。意思是说,我的格调和当时人不一样,心情却和隐士能相提比例;虽然长年生活在帝都,但却不知道权贵的门朝哪个方向开。
这话听着耳熟,没错,“诗仙”李白也曾说过:“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不过,李大诗人这是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权贵真给他笑脸,他跑得比谁都欢。
天宝十二年(753),张继凭真本事考中进士。大历末年,授官检校祠部员外郎,外派到洪州当盐铁判官,相当于盐铁行业的“国税官员”。在那里,他踏踏实实干好本职工作,不扯皮、不躺平,“辄有政声”。大约779年,张继夫妻都死于洪州,“群主”刘长卿还写诗悼念:
恸哭钟陵下,东流与别离。
二星来不返,双剑没相随。
……
世难愁归路,家贫缓葬期。
……
作为一名掌管国家财赋的政府官员,张继死后竟然没钱安葬,还需要缓期举行葬礼,清廉的让人想想都要哭。
二
那些年,张继每到一个地方,都有“直播带景”的习惯,比如《洛阳作》《晚次淮阳》《游灵岩》《宿白马诗》等。
这天,张继乘船停泊在苏州城外吴江上的枫桥歇息,江南水乡夜晚幽美的景色,吸引着这位满怀旅愁的游子。但时值深秋,在茫茫夜色中,刺骨的寒意从四面八方向他夜泊的小船涌来,他虽然裹紧了棉被,但仍然感觉到一阵阵孤寂清寒。
睡不着了,索性披衣而起写篇“小作文”吧。
你要写寒就不能只写寒,要写月落的光影惊醒了乌鸦啼鸣,要写霜华漫天;你要写愁就不能只写愁,要写江边的枫树和点点渔火,要写旅人的无眠……
那一刻,张继“小宇宙”爆炸,挥笔写下了四句千古绝唱: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这首《枫桥夜泊》,远景、近景、明暗、层次交相辉映,将残月、栖鸦、江枫、渔火写得妙趣横生。
寒山寺在枫桥西一里,相传唐初诗僧寒山曾住在这里,因此得名。今人刘学楷说:“枫桥的诗意美,有了这所古刹,便带上了历史文化色泽,而显得更加丰富,动人遐想。因此,这寒山寺‘夜半钟声’也就仿佛回荡着历史的回声,渗透着宗教的情思,而给人以一种古雅庄严之感了。”
那一夜,《枫桥夜泊》开始“火出圈”,脍炙人口、名驰中外,被无数人奉为圭臬。
比如宋人孙觌就写有《再宿枫桥》:
白发重来一梦中,
青山不改旧时容。
乌啼月落寒山寺,
欹枕犹闻夜半钟。
明代高启佩服地说:
画桥三百映江城,
诗里枫桥独有名。
几度经过忆张继,
乌啼月落又钟声。
清人孙枝蔚更是满怀深情:
依旧钟声夜半过,
谁如张继善吟哦?
老夫独少诗中酒,
始觉平生怨愤多。
不过,有佩服到五体投地的,就有“鸡蛋里挑骨头”的,大文豪欧阳修跳出来就是当头一炮:“‘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句子是很棒的,但半夜三更不是打钟的时候,这根本就是病句嘛!”
欧阳修把他的观点写在《六一诗话》里,然后美滋滋地洗洗睡了。
不过,张继的“粉丝”可没闲着,纷纷找出证据“拍”向欧阳修。
有“粉丝”说:“我在《南史》中找到了半夜钟的典故。”
还有“粉丝”说:“白居易的诗中也有半夜打钟的句子,比如‘新秋松影下,半夜钟声后。’”
更有“粉丝”说:“皇甫冉的诗句‘秋深临水月,夜半隔山钟’不也是明证吗?”
……
所以,“专家”也是有知识盲点的。
三
由于《枫桥夜泊》写得太过美感,许多文人墨客就琢磨着把此诗勒石刻碑。据《寒山寺志》记载,第一个“吃螃蟹”的是宋人王珪。
王珪是北宋仁宗时的宰相,元丰六年封为郇国公,罢相后住在苏州,写了这首诗刻在石碑上。据说写碑文的时候,王珪家有亲人去世,所以碑上没有署名。
到了明代,由于年代久远,王珪所书的石碑可能毁于战火,早就找不到了,所以人们又请“吴中四才子”之一的文徵明重写碑文。历经上百年风吹雨打,到了清代,这块碑已经漫漶不清,也就残存“霜、啼、姑、苏”几个字。
光绪三十二年(1906)秋末,江苏巡抚陈夔龙重修寒山寺,请到清末名士、经学大师俞樾手书了《枫桥夜泊》第三块石碑。俞樾你没听说过,也不怪你,但如果你连章太炎也不知道,这就不应该了。没错,章太炎就是俞樾的学生。当时,俞樾已是86岁高龄,接到这个任务后倍感光荣,挥毫泼墨、一气呵成。没想到的是,这幅书法作品竟成了俞樾的绝笔,因为这年的12月,他病逝了。
1936年,苏州名画家吴湖帆以为俞樾写的碑石失传了,于是就想请张继补写《枫桥夜泊》的诗文重刻一块石碑。此张继非彼张继,他字溥泉,河北沧州人,也是位诗人。
吴湖帆虽然知道张继的大名,但两个人并不认识,于是就把这事儿委托给濮一乘。张继一听,也感到十分荣幸,就说:“我早就倾慕寒山寺这个名胜古迹了,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也没去过。承蒙湖帆先生认为我的名字和唐代张继同名,让我书写碑文,这是看得起我。不过,我的‘继’字是‘恒久’的意思,可不敢和人家唐代大诗人比肩。”于是,他很快就写好了碑文。
吴湖帆在等待张继碑文的时候,却看到报纸上刊登张继去世的消息,就很后悔,想着这件事早点办就好了。没想到过了几天,收到了濮一乘寄来的写本,附信中说:“这是张继生前一日所写。”吴湖帆悲喜交集,立刻嘱咐一位叫黄怀觉的工匠刻在石碑上。
从此,俞樾的诗碑和张继的诗碑并列于寒山寺中。
1939年,时值抗日战争,汉奸梁鸿志在南京成立了伪“维新政府”。当时,日本大阪的《朝日新闻》社要举办大东亚博览会,为了撑门面,点名让伪政府把俞樾书写的那块诗碑运过去。
汉奸们只是坏,并不傻。知道把真迹孝敬了主子,肯定是厕所里面扔炸弹——激起民愤(粪),所以就请苏州有名的刻石师傅钱荣初刻了一块赝品。要说大师就是大师,这块石碑简直可以以假乱真。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块复制品也没有运送到日本,就留在了南京。
一首诗,引出这么多故事和佳话,不能不说唐代诗人张继的伟大。让我们以清人邹福宝的一副对联来做结束语吧:
尘劫历一千余年,重复旧观,幸有名贤来做主;
诗人题二十八字,长留胜迹,可知佳句不须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