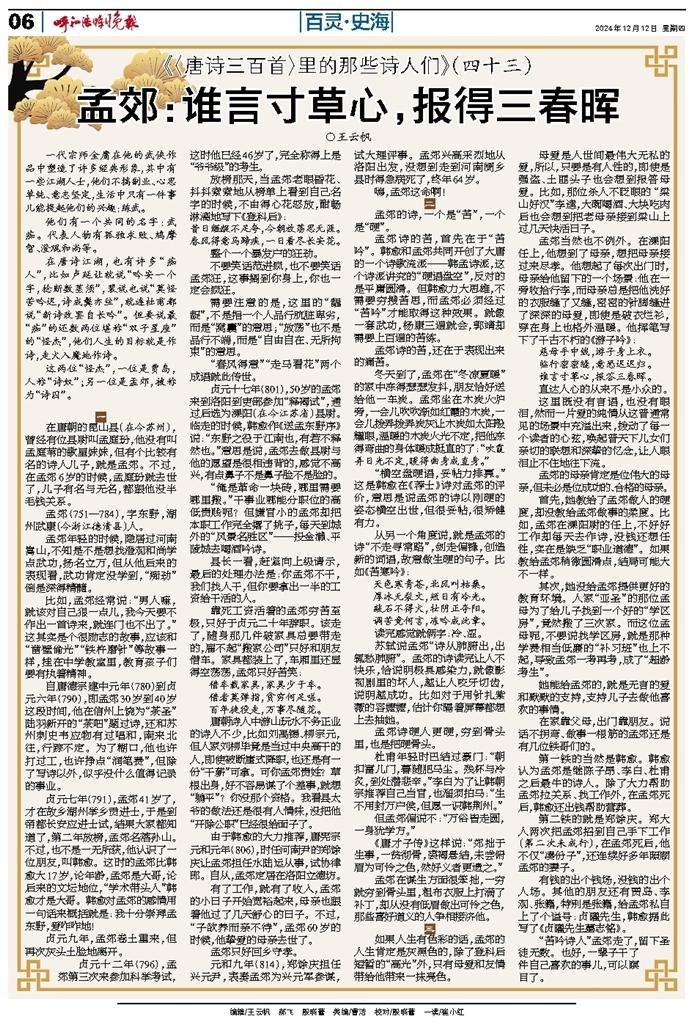一代宗师金庸在他的武侠作品中塑造了许多经典形象,其中有一些江湖人士,他们不搞副业、心思单纯、意志坚定,生活中只有一件事儿能提起他们的兴趣:练武。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武痴。代表人物有孤独求败、鸠摩智、澄观和尚等。
在唐诗江湖,也有许多“痴人”,比如卢延让就说“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裴说也说“莫怪苦吟迟,诗成鬓亦丝”,就连杜甫都说“新诗改罢自长吟”。但要说最“痴”的还数两位堪称“双子星座”的“怪杰”,他们人生的目标就是作诗,走火入魔地作诗。
这两位“怪杰”,一位是贾岛,人称“诗奴”;另一位是孟郊,被称为“诗囚”。
一
在唐朝的昆山县(在今苏州),曾经有位县尉叫孟庭玢,他没有叫孟庭苇的歌星妹妹,但有个比较有名的诗人儿子,就是孟郊。不过,在孟郊6岁的时候,孟庭玢就去世了,儿子有名与无名,都跟他没半毛钱关系。
孟郊(751—784),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县)人。
孟郊年轻的时候,隐居过河南嵩山,不知是不是想找澄观和尚学点武功,扬名立万,但从他后来的表现看,武功肯定没学到,“痴劲”倒是深得精髓。
比如,孟郊经常说:“男人嘛,就该对自己狠一点儿,我今天要不作出一首诗来,就连门也不出了。”这其实是个很励志的故事,应该和“凿壁偷光”“铁杵磨针”等故事一样,挂在中学教室里,教育孩子们要有执着精神。
自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到贞元六年(790),即孟郊30岁到40岁这段时间,他在信州上饶为“茶圣”陆羽新开的“茶吧”题过诗,还和苏州刺史韦应物有过唱和,南来北往,行踪不定。为了糊口,他也许打过工,也许挣点“润笔费”,但除了写诗以外,似乎没什么值得记录的事业。
贞元七年(791),孟郊41岁了,才在故乡湖州举乡贡进士,于是到帝都长安应进士试,结果大家都知道了,第二年放榜,孟郊名落孙山。不过,也不是一无所获,他认识了一位朋友,叫韩愈。这时的孟郊比韩愈大17岁,论年龄,孟郊是大哥,论后来的文坛地位,“学术带头人”韩愈才是大哥。韩愈对孟郊的感情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我十分崇拜孟东野,爱咋咋地!
贞元九年,孟郊卷土重来,但再次灰头土脸地离开。
贞元十二年(796),孟郊第三次来参加科举考试,这时他已经46岁了,完全称得上是“爷爷级”的考生。
放榜那天,当孟郊老眼昏花、抖抖索索地从榜单上看到自己名字的时候,不由得心花怒放,酣畅淋漓地写下《登科后》: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整个一个暴发户的狂劲。
不要笑话范进疯,也不要笑话孟郊狂,这事搁到你身上,你也一定会疯狂。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龌龊”,不是指一个人品行肮脏卑劣,而是“窝囊”的意思;“放荡”也不是品行不端,而是“自由自在、无所拘束”的意思。
“春风得意”“走马看花”两个成语就此传世。
贞元十七年(801),50岁的孟郊来到洛阳到吏部参加“释褐试”,通过后选为溧阳(在今江苏省)县尉。临走的时候,韩愈作《送孟东野序》说:“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也。”意思是说,孟郊去做县尉与他的愿望是很相违背的,感觉不高兴,有点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
“俺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干事业哪能分职位的高低贵贱呢?但嫌官小的孟郊却把本职工作完全撂了挑子,每天到城外的“风景名胜区”——投金濑、平陵城去喝酒吟诗。
县长一看,赶紧向上级请示,最后的处理办法是:你孟郊不干,我们找人干,但你要拿出一半的工资给干活的人。
靠死工资活着的孟郊穷苦至极,只好于贞元二十年辞职。该走了,随身那几件破家具总要带走的,雇不起“搬家公司”只好和朋友借车。家具都装上了,车厢里还显得空荡荡,孟郊只好苦笑:
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
借者莫弹指,贫穷何足嗟。
百年徒役走,万事尽随花。
唐朝诗人中游山玩水不务正业的诗人不少,比如刘禹锡、柳宗元,但人家刘柳毕竟是当过中央高干的人,即使被断崖式降职,也还是有一份“干薪”可拿。可你孟郊贵姓?草根出身,好不容易谋了个差事,就想“躺平”?你没那个资格。我看县太爷的做法还是很有人情味,没把他“开除公职”已经很给面子了。
由于韩愈的大力推荐,唐宪宗元和元年(806),时任河南尹的郑馀庆让孟郊担任水陆运从事,试协律郎。自从,孟郊定居在洛阳立德坊。
有了工作,就有了收入,孟郊的小日子开始宽裕起来,母亲也跟着他过了几天舒心的日子。不过,“子欲养而亲不待”,孟郊60岁的时候,他挚爱的母亲去世了。
孟郊只好回乡守孝。
元和九年(814),郑馀庆担任兴元尹,表奏孟郊为兴元军参谋,试大理评事。孟郊兴高采烈地从洛阳出发,没想到走到河南阌乡县时得急病死了,终年64岁。
嗨,孟郊这命啊!
二
孟郊的诗,一个是“苦”,一个是“硬”。
孟郊诗的苦,首先在于“苦吟”。韩愈和孟郊共同开创了大唐的一个诗歌流派——韩孟诗派,这个诗派讲究的“硬语盘空”,反对的是平庸圆滑。但韩愈力大思雄,不需要穷搜苦思,而孟郊必须经过“苦吟”才能取得这种效果。就像一套武功,杨康三遍就会,郭靖却需要上百遍的苦练。
孟郊诗的苦,还在于表现出来的痛苦。
冬天到了,孟郊在“冬凉夏暖”的家中冻得瑟瑟发抖,朋友恰好送给他一车炭。孟郊坐在木炭火炉旁,一会儿吹吹渐如红霞的木炭,一会儿拨弄拨弄炭灰让木炭如太阳般耀眼,温暖的木炭火光不定,把他冻得弯曲的身体暖成挺直的了:“吹霞弄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
“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这是韩愈在《荐士》诗对孟郊的评价,意思是说孟郊的诗以刚硬的姿态横空出世,但很妥帖,很矫健有力。
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孟郊的诗“不走寻常路”,剑走偏锋,创造新的词语,故意做生硬的句子。比如《苦寒吟》:
天色寒青苍,北风叫枯桑。
厚冰无裂文,短日有冷光。
敲石不得火,壮阴正夺阳。
调苦竟何言,冻吟成此章。
读完感觉就俩字:冷、涩。
苏轼说孟郊“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孟郊的诗读完让人不快乐,恰说明极具感染力,就像影视剧里的坏人,越让人咬牙切齿,说明越成功。比如对于用针扎紫薇的容嬷嬷,估计你隔着屏幕都想上去抽她。
孟郊诗硬人更硬,穷到骨头里,也是把硬骨头。
杜甫年轻时巴结过豪门:“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李白为了让韩朝宗推荐自己当官,也溜须拍马:“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但孟郊偏说不:“万俗皆走圆,一身犹学方。”
《唐才子传》这样说:“郊拙于生事,一贫彻骨,裘褐悬结,未尝俯眉为可怜之色,然好义者更遗之。”
孟郊在谋生方面很笨拙,一穷就穷到骨头里,粗布衣服上打满了补丁,却从没有低眉做出可怜之色,那些喜好道义的人争相接济他。
三
如果人生有色彩的话,孟郊的人生肯定是灰黑色的,除了登科后短暂的“高光”外,只有母爱和友情带给他带来一抹亮色。
母爱是人世间最伟大无私的爱,所以,只要是有人性的,即使是强盗、土匪头子也会想到报答母爱。比如,那位杀人不眨眼的 “梁山好汉”李逵,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后也会想到把老母亲接到梁山上过几天快活日子。
孟郊当然也不例外。在溧阳任上,他想到了母亲,想把母亲接过来尽孝。他想起了每次出门时,母亲给他留下的一个场景:他在一旁收拾行李,而母亲总是把他洗好的衣服缝了又缝,密密的针脚缝进了深深的母爱,即使是破衣烂衫,穿在身上也格外温暖。他挥笔写下了千古不朽的《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答三春晖。
直达人心的从来不是小众的。
这里既没有言语,也没有眼泪,然而一片爱的纯情从这普通常见的场景中充溢出来,拨动了每一个读者的心弦,唤起普天下儿女们亲切的联想和深挚的忆念,让人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孟郊的母亲肯定是位伟大的母亲,但未必是位成功的、合格的母亲。
首先,她教给了孟郊做人的硬度,却没教给孟郊做事的柔度。比如,孟郊在溧阳尉的任上,不好好工作却每天去作诗,没钱还想任性,实在是缺乏“职业道德”。如果教给孟郊稍微圆滑点,结局可能大不一样。
其次,她没给孟郊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人家“亚圣”的那位孟母为了给儿子找到一个好的“学区房”,竟然搬了三次家。而这位孟母呢,不要说找学区房,就是那种学费相当低廉的“补习班”也上不起,导致孟郊一考再考,成了“超龄考生”。
她能给孟郊的,就是无言的爱和默默的支持,支持儿子去做他喜欢的事情。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说话不拐弯、做事一根筋的孟郊还是有几位铁哥们的。
第一铁的当然是韩愈。韩愈认为孟郊是继陈子昂、李白、杜甫之后最牛的诗人。除了大力帮助孟郊拉关系、找工作外,在孟郊死后,韩愈还出钱帮助营葬。
第二铁的就是郑馀庆。郑大人两次把孟郊招到自己手下工作(第二次未成行),在孟郊死后,他不仅“凑份子”,还连续好多年照顾孟郊的妻子。
有钱的出个钱场,没钱的出个人场。其他的朋友还有贾岛、李观、张籍,特别是张籍,给孟郊私自上了个谥号:贞曜先生,韩愈据此写了《贞曜先生墓志铭》。
“苦吟诗人”孟郊走了,留下圣徒无数。也好,一辈子干了件自己喜欢的事儿,可以瞑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