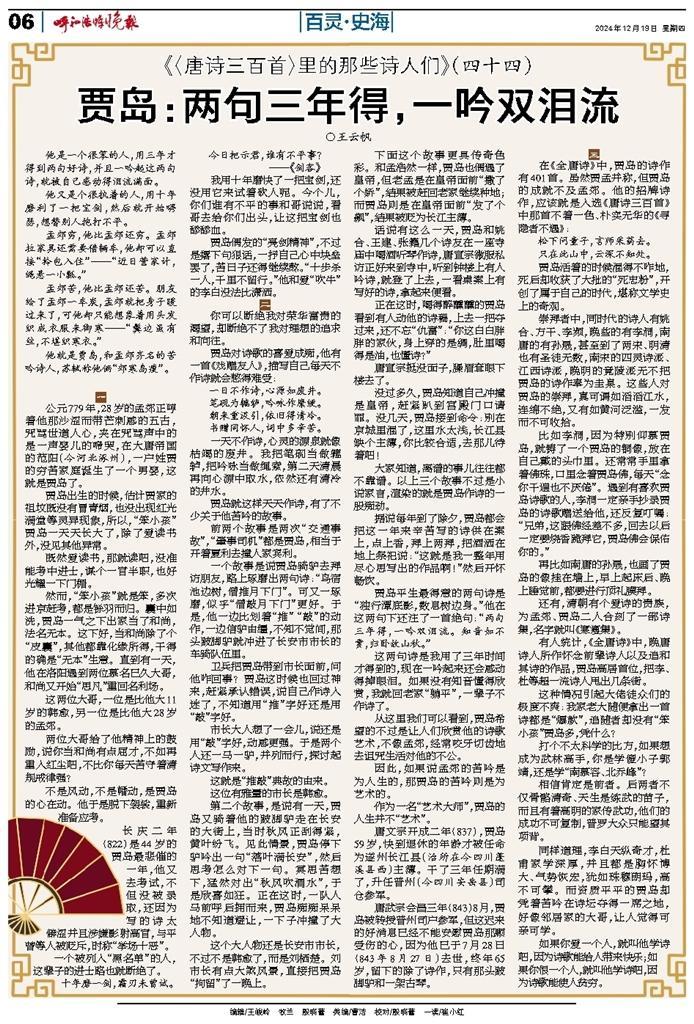他是一个很笨的人,用三年才得到两句好诗,并且一吟起这两句诗,就被自己感动得泪流满面。
他又是个很执着的人,用十年磨利了一把宝剑,然后就开始嘚瑟,想替别人抱打不平。
孟郊穷,他比孟郊还穷。孟郊拉家具还需要借辆车,他却可以直接“拎包入住”——“近日营家计,绳悬一小瓢。”
孟郊苦,他比孟郊还苦。朋友给了孟郊一车炭,孟郊就把身子暖过来了,可他却只能想象着用头发织成衣服来御寒——“鬓边虽有丝,不堪织寒衣。”
他就是贾岛,和孟郊齐名的苦吟诗人,苏轼称他俩“郊寒岛瘦”。
一
公元779年,28岁的孟郊正哼着他那沙涩而带芒刺感的五古,咒骂世道人心,夹在咒骂声中的是一声婴儿的啼哭,在大唐帝国的范阳(今河北涿州),一户姓贾的穷苦家庭诞生了一个男婴,这就是贾岛了。
贾岛出生的时候,估计贾家的祖坟既没有冒青烟,也没出现红光满堂等灵异现象,所以,“笨小孩”贾岛一天天长大了,除了爱读书外,没见其他异常。
既然爱读书,那就读吧,没准能考中进士,谋个一官半职,也好光耀一下门楣。
然而,“笨小孩”就是笨,多次进京赶考,都是铩羽而归。囊中如洗,贾岛一气之下出家当了和尚,法名无本。这下好,当和尚除了个“皮囊”,其他都靠化缘所得,干得的确是“无本”生意。直到有一天,他在洛阳遇到两位慕名已久大哥,和尚又开始“思凡”重回名利场。
这两位大哥,一位是比他大11岁的韩愈,另一位是比他大28岁的孟郊。
两位大哥给了他精神上的鼓励,说你当和尚有点屈才,不如再重入红尘吧,不比你每天苦守着清规戒律强?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贾岛的心在动。他于是脱下袈裟,重新准备应考。
长庆二年(822)是44岁的贾岛最悲催的一年,他又去考试,不但没被录取,还因为写的诗太僻涩并且涉嫌影射高官,与平曾等人被贬斥,时称“举场十恶”。
一个被列入“黑名单”的人,这辈子的进士路也就断绝了。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
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剑客》
我用十年磨快了一把宝剑,还没用它来试着砍人呢。今个儿,你们谁有不平的事和哥说说,看哥去给你们出头,让这把宝剑也舔舔血。
贾岛偶发的“亮剑精神”,不过是撂下句狠话,一抒自己心中块垒罢了,苦日子还得继续熬。“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他和爱“吹牛”的李白没法比潇洒。
二
你可以断绝我对荣华富贵的渴望,却断绝不了我对理想的追求和向往。
贾岛对诗歌的喜爱成痴,他有一首《戏赠友人》,描写自己每天不作诗就会憋得难受:
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
笔砚为辘轳,吟咏作縻绠。
朝来重汲引,依旧得清冷。
书赠同怀人,词中多辛苦。
一天不作诗,心灵的源泉就像枯竭的废井。我把笔砚当做辘轳,把吟咏当做绳索,第二天清晨再向心源中取水,依然还有清冷的井水。
贾岛就这样天天作诗,有了不少关于他苦吟的故事。
前两个故事是两次“交通事故”,“肇事司机”都是贾岛,相当于开着夏利去撞人家宾利。
一个故事是说贾岛骑驴去拜访朋友,路上琢磨出两句诗:“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可又一琢磨,似乎“僧敲月下门”更好。于是,他一边比划着“推” “敲”的动作,一边信驴由缰,不知不觉间,那头跛脚驴就冲进了长安市市长的车骑队伍里。
卫兵把贾岛带到市长面前,问他咋回事?贾岛这时候也回过神来,赶紧承认错误,说自己作诗入迷了,不知道用“推”字好还是用“敲”字好。
市长大人想了一会儿,说还是用“敲”字好,动感更强。于是两个人还一马一驴,并列而行,探讨起诗文写作来。
这就是“推敲”典故的由来。
这位有雅量的市长是韩愈。
第二个故事,是说有一天,贾岛又骑着他的跛脚驴走在长安的大街上,当时秋风正刮得紧,黄叶纷飞。见此情景,贾岛停下驴吟出一句“落叶满长安”,然后思考怎么对下一句。冥思苦想下,猛然对出“秋风吹渭水”,于是欣喜如狂。正在这时,一队人马前呼后拥而来,贾岛痴痴呆呆地不知道避让,一下子冲撞了大人物。
这个大人物还是长安市市长,不过不是韩愈了,而是刘栖楚。刘市长有点大煞风景,直接把贾岛“拘留”了一晚上。
下面这个故事更具传奇色彩。和孟浩然一样,贾岛也偶遇了皇帝,但老孟是在皇帝面前“撒了个娇”,结果被赶回老家继续种地;而贾岛则是在皇帝面前“发了个飙”,结果被贬为长江主簿。
话说有这么一天,贾岛和姚合、王建、张籍几个诗友在一座寺庙中喝酒听琴作诗,唐宣宗微服私访正好来到寺中,听到钟楼上有人吟诗,就登了上去,一看桌案上有写好的诗,拿起来便看。
正在这时,喝得醉醺醺的贾岛看到有人动他的诗稿,上去一把夺过来,还不忘“仇富”:“你这白白胖胖的家伙,身上穿的是绸,肚里喝得是油,也懂诗?”
唐宣宗挺没面子,臊眉耷眼下楼去了。
没过多久,贾岛知道自己冲撞是皇帝,赶紧趴到宫殿门口请罪。没几天,贾岛接到命令:别在京城里混了,这里水太浅,长江县缺个主簿,你比较合适,去那儿待着吧!
大家知道,离谱的事儿往往都不靠谱。以上三个故事不过是小说家言,渲染的就是贾岛作诗的一股痴劲。
据说每年到了除夕,贾岛都会把这一年来辛苦写的诗供在案上,点上香,拜上两拜,把酒洒在地上祭祀说:“这就是我一整年用尽心思写出的作品啊!”然后开怀畅饮。
贾岛平生最得意的两句诗是“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他在这两句下还注了一首绝句:“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
这两句诗是我用了三年时间才得到的,现在一吟起来还会感动得掉眼泪。如果没有知音懂得欣赏,我就回老家“躺平”,一辈子不作诗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贾岛希望的不过是让人们欣赏他的诗歌艺术,不像孟郊,经常咬牙切齿地去诅咒生活对他的不公。
因此,如果说孟郊的苦吟是为人生的,那贾岛的苦吟则是为艺术的。
作为一名“艺术大师”,贾岛的人生并不“艺术”。
唐文宗开成二年(837),贾岛59岁,快到退休的年龄才被任命为遂州长江县(治所在今四川蓬溪县西)主簿。干了三年任期满了,升任普州(今四川安岳县)司仓参军。
唐武宗会昌三年(843)8月,贾岛被转授普州司户参军,但这迟来的好消息已经不能安慰贾岛那颗受伤的心,因为他已于7月28日(843年8月27日)去世,终年65岁,留下的除了诗作,只有那头跛脚驴和一架古琴。
三
在《全唐诗》中,贾岛的诗作有401首。虽然贾孟并称,但贾岛的成就不及孟郊。他的招牌诗作,应该就是入选《唐诗三百首》中那首不着一色、朴实无华的《寻隐者不遇》: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贾岛活着的时候混得不咋地,死后却收获了大批的“死忠粉”,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时代,堪称文学史上的奇观。
崇拜者中,同时代的诗人有姚合、方干、李频,晚些的有李洞,南唐的有孙晟,甚至到了两宋、明清也有圣徒无数,南宋的四灵诗派、江西诗派,晚明的竟陵派无不把贾岛的诗作奉为圭臬。这些人对贾岛的崇拜,真可谓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有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
比如李洞,因为特别仰慕贾岛,就铸了一个贾岛的铜像,放在自己戴的头巾里。还常常手里拿着佛珠,口里念着贾岛佛,每天“念你千遍也不厌倦”。遇到有喜欢贾岛诗歌的人,李洞一定亲手抄录贾岛的诗歌赠送给他,还反复叮嘱:“兄弟,这跟佛经差不多,回去以后一定要烧香跪拜它,贾岛佛会保佑你的。”
再比如南唐的孙晟,也画了贾岛的像挂在墙上,早上起床后、晚上睡觉前,都要进行顶礼膜拜。
还有,清朝有个爱诗的贵族,为孟郊、贾岛二人合刻了一部诗集,名字就叫《寒瘦集》。
有人统计,《全唐诗》中,晚唐诗人所作怀念前辈诗人以及追和其诗的作品,贾岛高居首位,把李、杜等超一流诗人甩出几条街。
这种情况引起大佬徒众们的极度不爽:我家老大随便拿出一首诗都是“爆款”,追随者却没有“笨小孩”贾岛多,凭什么?
打个不太科学的比方,如果想成为武林高手,你是学傻小子郭靖,还是学“南慕容、北乔峰”?
相信肯定是前者。后两者不仅骨骼清奇、天生是练武的苗子,而且有着高明的家传武功,他们的成功不可复制,普罗大众只能望其项背。
同样道理,李白天纵奇才,杜甫家学深厚,并且都是胸怀博大、气势恢宏,犹如珠穆朗玛,高不可攀。而资质平平的贾岛却凭着苦吟在诗坛夺得一席之地,好像邻居家的大哥,让人觉得可亲可学。
如果你爱一个人,就叫他学诗吧,因为诗歌能给人带来快乐;如果你恨一个人,就叫他学诗吧,因为诗歌能使人贫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