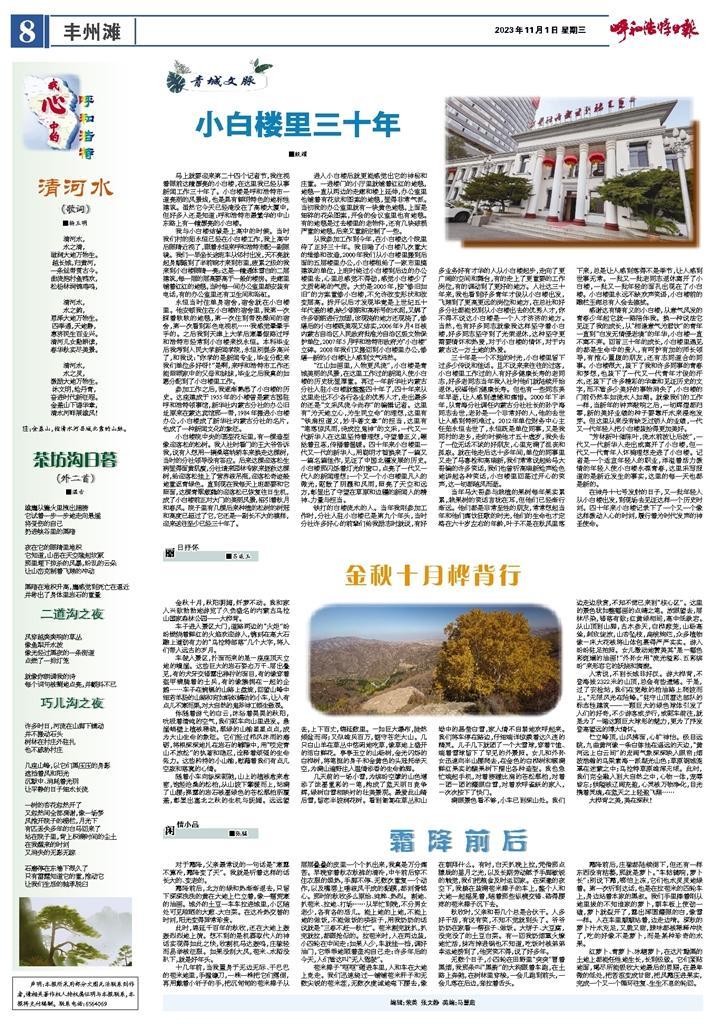■张猛
对于霜降,父亲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寒露不算冷,霜降变了天”。我就是听着这样的话长大的、变老的。
霜降前后,北方的绿和热渐渐退去,只留下深深浅浅的黄在大地上伫立着,像一幅荒寒的油画。城外的土豆一车车拉进城里,小区随处可见晾晒的大葱、大白菜。在这冷热交替的时刻,阳光变得异常珍贵。
此时,绵延千百年的秋收,还在大地上轰轰烈烈地上演。想不到的是机器取代人的神话实现得如此之快,收割机马达轰鸣,庄稼轻而易举被征服。如果没刮大风,苞米、水稻没趴下,就是好年头。
十几年前,当我置身于无边无际、干巴巴的苞米地里,手握镰刀,一株一株把它们撂倒,再用戴着小钎子的手,把沉甸甸的苞米棒子从层层叠叠的皮里一个个扒出来,我真是万分痛苦。早晚穿着秋衣秋裤的清冷,中午前后穿不住衣服的燥热,手脚不停、无数次重复一个动作,以及嘴唇上唾液风干成的黏膜,都刻骨铭心。那时的秋收多么原始、纯粹、热烈。 割地、扒苞米、拉地、打场……从早忙到晚,不分男女老少,各有各的活儿。能上地的上地,不能上地的做饭,不能做饭的哄孩子,用我奶奶的话说就是“三春不赶一秋忙”。苞米割完就扒,扒完就拉,都跟抢似的。拉苞米时,人在两边装,小四轮在中间走;如果人少,车就挂一挡,调好油门,它乖乖地顺着垄沟自己走;许多年后的今天,人们管这叫“无人驾驶”。
苞米棒子“哐哐”砸进车里,人和车在大地上竞走。我们迅速绕过一铺铺苞米秆子和无数尖锐的苞米茬,无数次虔诚地弯下腰去,像在朝拜什么。有时,白天扒晚上拉,凭借那点朦胧的星月之光,以及长期劳动赋予手脚敏锐的触觉,我们把粮食及时运回家。在深邃的夜空下,我躺在装满苞米棒子的车上,整个人和大地一起摇晃着,随着那些纵横交错、硌得腰疼的苞米棒子沉下去。
秋收时,父亲和哥几个总是合伙干。人多好干活,有说有笑,不知不觉就到头了。爷爷奶奶在家看一帮孩子、做饭。大饼子、大豆腐,没完没了的土豆白菜。有一回我奶烟熏火燎地忙活,抹布掉进锅也不知道,吃饭时被弟弟幸运地捞到了,他哭笑不得,说了好多年。
无数个日子,小四轮在田野里“突突”冒着黑烟,我那条叫“黑箭”的大狗跟着车跑,在土路上奔驰,在树林里穿梭,一会儿跑到前头,一会儿落在后边,耷拉着舌头。
霜降前后,庄稼都陆续倒下,但还有一样东西没有枯萎,那就是萝卜。“车轱辘响,萝卜长”;别说下霜,哪怕上冻,它们也水灵灵地绿着。第一次听到这话,也是在拉苞米的四轮车上,身边站着本家的黑叔。我们手里捧着刚从地里拔的不知谁家的萝卜,朝车板上使劲一磕,萝卜就裂开了,露出浑圆耀眼的白,像雪一样。人在车里颠颠站着,边走边啃。深秋的萝卜汁水充足,又脆又甜,辣味都被稀释冲淡了,吃的好像不是萝卜,而是某种珍奇的水果。
红萝卜、青萝卜、冰糖萝卜,在这片黝黑的土地上都能任性地生长,长到极致。它们紧贴地面,竭尽所能吸收大地最后的恩赐,在最卑微的低处,把苦涩变成甘甜,把风霜压进果实,完成一个又一个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轮回。